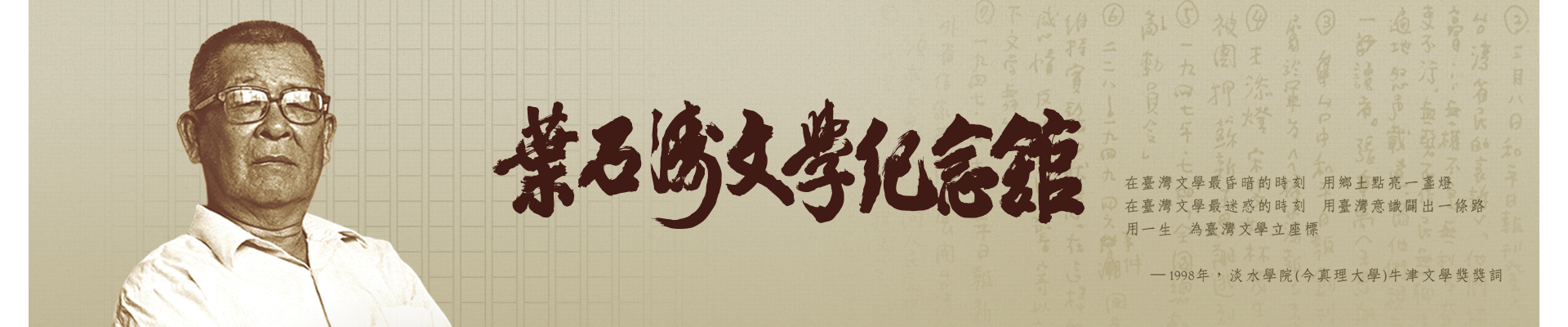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吃豬皮的日子〉
我很早就知道府城有個馬兵營街,原本是連雅堂故居所在的地方。日據時代連雅堂的故居早已蕩然無存,變成富麗堂皇很有殖民地衙門風格的地方法院了。地方法院此類打官司的地方,跟我家完全是扯不上關係的。我們從來不跟人打官司,所以除非路過,否則我很少走到這附近來。可是命運的安排,我有一段時期幾乎生活在這馬兵營街。
入夜以後的馬兵營街一片漆黑。但是離這兒不遠的下大道良皇宮前卻是燈火燦爛、人生嘈雜的夜市。這兒有各式各樣的小吃攤,位在西門町尾,離新町(妓女街)不遠,所以生意特別興隆。
每天晚上我從馬兵營街拖著疲憊的步伐來到下大道,就常看到一輪明月或弦月掛在西邊的夜空上。那時候快接近午夜,大多數的攤子都打烊了。但是我一點也不著急,我知道葛根伯的攤子一定還沒收。葛根伯所賣的東西跟別人有別。一隻大鐵鍋裡煮著豬皮、蘿蔔、油豆腐之類的東西。說起來跟日本的某種火鍋相似。但是材料不同,日本人煮的是蒟蒻、豆腐、芋頭、魚糕此類較高貴的東西。而葛根伯搜羅得來的盡是些人家看不起的卑賤食物。一大碗才賣兩塊錢。而且再添湯是免費的。如果我口袋裡有五塊錢的話,我可以買一杯紅標米酒或太白酒,以及一大碗豬皮湯來下酒,盡可喝得微醺了。但是適可而止是多困難的事,所以我往往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那時候,攤子上點著的是電石燈,所以喝到第二杯的時候,我已經醉眼矇矓起來。看不清葛根伯的的臉了。葛根伯本來是在新町〈妓女街〉幹活兒的藝人,聽說是替賣藝不賣身的藝旦清唱平劇時拉胡弓的,年老了以後,才來這兒擺攤子;其實這和新町的盛衰有關,以前那優雅的時候過去了,再沒有人有雅興去新町找藝旦聽清唱平劇,自然拉胡弓的也失了業,因此,這老頭也保持了一貫的古風,客人欠賬,向來不催。但也有缺點,從不勸止人家少喝一點。可是他也不見得是慷慨的,大碗裡的豬皮啃光了,他絕不添,只給你添湯。所以除非你聲明再付兩塊錢,否則那煮得並不爛的豬皮就再也吃不到了。我絕對不欠他的錢,可是常囊空如洗,往往只好已湯佐酒了。
這是民國四十幾年的事情。我當時孓然一身,在馬兵營街附近的自來水機構當臨時工友。每天的工作包括燒消毒實驗器材的蒸汽鍋、掃地倒垃圾、燒開水倒茶、抹桌子、跑郵局,以及諸如此類數不清的雜活兒。
晚上我執夜到十二點左右,這才離開辦公室回到家裡去,那時候滿腔悲苦無處可發洩,只好喝酒解愁了。
人落魄到這個地步也只好任人踐踏。在那荒蕪的五○年代裡,人能夠僥倖保存一條老命,從那惡魔島回來,也等於是獲得上地的垂憐,又有什麼不滿可言?糟糕的是我跟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小知識份子一樣,身無一技之長,真是個「無用的人」。我之所以淪落到變成一個臨時工友也是理所當然,否則三餐也無以為繼了。別以為我懷抱著某種托爾斯泰主義,以勞動換取麵包為榮才好。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葛根伯也有老婆孩子,所以有一天晚上,照例坐在那汙垢積得黑亮的木凳時,抬頭一看,看見天邊蒼白的眉形月和一個勤快地洗碗的年輕姑娘而傻了眼。我那天晚上興緻很不錯,剛領了幾十塊值夜費,打算喝個痛快。但是一個姑娘在場,這就不好喝得醜態百出了。
那年輕姑娘抬起頭來,用滿臉詫異的表情凝視了我一會兒,又很快的別過頭去,好像要咬耳根似的,把嘴湊近老頭的耳朵邊去,細聲講了幾句話。那老頭邊聽著,邊「呵!」「呵!」的發出幾聲讚嘆聲。電石燈搖晃微弱的光,把這光景朦朧地照出來。
「要不要喝酒?」葛根伯說。
「這還用說嗎?」我不高興的回答。
葛根伯一點也不生氣。拿了一個大茶杯滿滿的倒了米酒,大茶杯可是要四塊錢的,我只要先來小茶杯就行,但是我倒不去說他,反正,我口袋裡的錢還應付得了,那一大碗豬皮湯和往常不同,似乎豬皮多,蘿蔔少、而且香菜、香油也放得特別多,非常香。我埋頭吃、喝,竟忘了老頭和年輕姑娘。人窮志短,可能吃相也很難看的吧,奇怪的是,我吃完了一碗豬皮湯,年輕的姑娘又給我添了一碗;不只是湯,同樣有許多豬皮和油豆腐,茶杯的酒喝乾了,不待我吩咐,那年輕姑娘自作主張倒得滿滿的,那葛根伯忙著照顧別的客人,留那姑娘特地服侍我,不說一句話,臉上倒浮現著嘉許伊行為似的微笑。我把一切看在眼裡,驀地萌生一絲邪惡之念:我以為他們倆串通好了,來賺取我口袋裡的幾十塊錢了,這也無妨,還不至於弄得我一窮二白吧?
等到我覺得夜涼如水的時候,我這才發覺我已經喝得酩酊大醉,周圍已沒有客人了。
「多少錢?」我說。
「四塊錢。」葛根伯平靜的說。
「四塊錢?你沒有算錯?」我在心裡盤算起來。酒大概喝了三大杯,是十二塊。豬皮湯吃了兩大碗,是四塊,共十六塊錢才對。我把十六塊放在那油潰斑斑的木桌上。
「我說四塊錢,就是四塊錢,錯不了。」那葛根伯忽然生氣起來,從一堆錢裡只拿了四塊硬幣,其餘硬塞回到我口袋裏去。
「秋霞,妳送他回去,他醉了,連錢也算不清。」葛根伯說。
「不用,我自個兒會走回去,她是?」
「哦,她是我女兒。」葛根伯說
我再三推辭,但這老頭硬是不接受,一定要他女兒送我回去,我知道他的牛脾氣,只好隨他去。而這姑娘頂多十六、七歲,還稚幼得不知跟她說什麼才好。
我們倆就這樣,一起走下午夜的西門町,拖著長長的孤單的影子,走了約莫一刻鐘,那姑娘忽然開口說話了。
「老師,您家還在嶺後街那一條巷子盡頭嗎?」
「老師?妳是?」我驚出一身冷汗來,酒也醒了一半。
「您難道忘了?我是葛秋霞,六年孝班您班上的,那年學校開學不久,您就沒來上課了。我是班長,所以跟林校長到處打聽,才知道您在看守所坐牢,您不是收到毛巾、香皂、牙刷之類的東西嗎?那是班上同學出錢買來送老師的。」
秋霞用黯然的聲音說起前塵往事來,這觸到了我心裡的傷痕,我呻吟起來,如果她不在,我一定放聲大哭無疑。
「我想起來了,我的確收到了你們所捐的東西。」我心裡喃喃的說,這些東西一直在我身邊,用壞了我也沒丟棄,一直到出獄還帶回來的呀,可是我並沒有說出來。
「老師,我爹說,您酒喝得太兇,而且現在的工作也不合您的身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應該另謀途徑才是。」秋霞悄悄地說,但那語意卻是毅然而堅決的。
「另謀途徑?」我有如被空氣槍打中的鴿子楞在那兒發呆了一陣子。
「是阿,人應該賺合乎自己身分的錢,譬如我爹,本是下賤的藝人,是個江湖客,賣豬皮湯謀生;他的錢賺得心安理得,我哪,是窮苦人家的女孩兒,幫傭賺錢也不辱沒了我,但是老師,您不同,您應該往上爬,您不應該如此墮落下去,我爹說,老師您太沒出息了。」
我淚眼模糊地望著那下弦月,久久說不出一句話,然後跟秋霞分手,決然往前走下去,第二天開始,我不再去上臨時工友的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