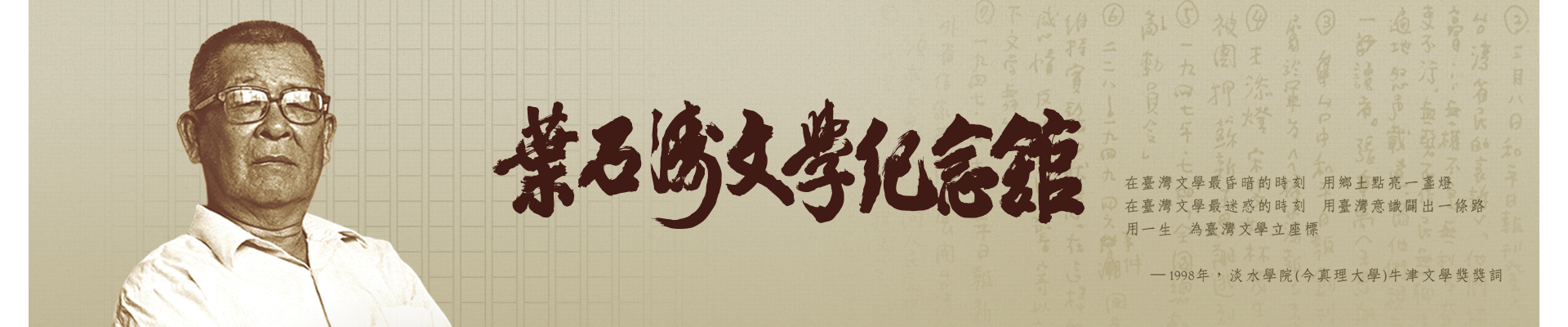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節錄自〈卡薩爾斯之琴〉
一、從打銀街到嶺後街(小說節錄)
當時,剛光復不久,坐落在N市打銀街的,原本像廟宇一樣富麗堂皇的祖宅,因為遭受盟軍B29的猛烈轟炸,早已蕩然無存,只剩下些斷垣頹壁可供我們掉幾滴傷心的輕淚。然而我家卻食指浩繁,尚有兩老,下有六個弟妹,侷促於兩間總共不到二十個塌塌米大的賃屋,整天價爭吵、喧嘩,弄得人人神經兮兮,如坐愁城。最後自為長子的我,拗不過眾口一詞的指謫和非難,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揮淚賣掉僅存的祖公屎,在嶺後街的一角落,購置兩房一廳看來頗不錯的屋瓦,這樣,大家勉強擠擠,道也能夠撐住遙遙欲墬的舊世家體面了。
二、搬家次日清晨,葉石濤父親對於新家的反應(小說節錄)
「爹!您早哇!」我說。
「咳!不早啦!」父親很不屑的說。我從來不會因他譏諷的口吻而有所不滿。她原本是地方上的士紳,滿腹經綸,有時難免談鋒銳利古怪,我早就習以為常了。大凡在日據時代,飽受日本仔欺凌而不屈服的舊式知識份子大都有這一種目中無人的傲骨。
「X依娘!」父親喀─的一聲又吐出一口濃痰,憤憤不平的咒罵;但這也並不能叫我喪氣,我自幼生長在他的一片頗不文雅的口頭禪聲浪中,早就養成不動肝火的涵養。
「爹!您今早氣色真好!」我滿不在乎地用天鵝絨般柔軟的聲音說。
「咳!我說錦仔!你買這房子可就上大當啦!」父親氣得臉色發青,巨大的喉核不停地上下移動。
「爹!我曉得這幢房子並不十全十美,也太狹窄了些。但,這年頭有棲身之處也算不錯啦!」我囁嚅的分辯。
「噯…噯…如今家道衰落,比不得往昔,有什麼好說呢?」大家勉強擠一擠也算不了什麼!就是,你瞧,這算是門嗎?進得來,卻出不去!」
父親用顫抖的手指氣虎虎地指著通往門口的小徑,一臉的傷心。我沿著他所指的小徑謹慎地掃視一番,到也沒看出有什麼值得傷心之處。原來,我這屋瓦被夾在兩堵高牆之中,前頭有一幢洋樓擋住。在洋樓和右邊高牆之間,只留著一條約莫三臺尺觀的小徑通往外面巷路,原本可能是舊世家深宅大院的後頭廂房。雖然如此,還不至於嚴重得只進得來,卻出不去。
「爹,昨天咱們簿也是進進出出好幾趟,暢行無阻嗎?」我據理力爭。
「騙肖!」又是一陣咆嘯:「哼,難道你以為我不知。你大妹早就回來告訴我,說那衣櫥,壓根兒就是進不了門,最後還不是央請鄰居開那扇門,才扛得進來!」我父親早已瞭若指掌,從容的指著鄰居家又編一睹高牆中間緊閉的板門。這一定是愛嚼舌根的大妹早告了一狀。
「這!這…不過就是搬進來時有一丁點麻煩罷了,咱們也不是打算天天搬家的呀!說不上什麼不方便!」我一肚子氣不便發洩,只好繼續反駁著。
「哈哼!你真是『馬鹿』的可愛!」我父親突然用一句日本話中最討他喜歡的。可惜他能夠學得來的近式些惡言穢語,好像他認為日本文化的精隨都濃縮結晶在這些話裡面似的。
「萬一我身上有了些什麼差錯怎麼出得去?」父親越來越悲傷,聲音暗啞了。
「有了什麼差錯?」我仍然如墬五里霧中懵懵然,不懂他底意思。
「你真是笨咕拉(窩囊胚也!),萬一我翹了辮子,棺材怎麼扛得出去?」他頗不情願地臉色越發鐵青了。
「哦,原來如此!」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也不覺跟著父親憂心了。然而當我仔細的揣詳父親紅潤的臉,魁梧的身材,而想起我阿公曾是前清武貢生的時候,心情稍微寬鬆起來,為父親的杞憂而覺得可笑。以他健壯的體格而言,再活個參十年也並非難事。倒是我這弱不禁風的不肖兒子七病八災的,也許沒福氣活到他那樣的一大把年紀呢!
「無論如何,這牆非拆掉往後退二尺不可,這事交給我辦!」父親雄赳赳的說著,握著拳,準備一番惡鬥的樣子。
「鄰家不知做什麼的?他們肯嗎?」我懷疑。
三、藝術主義至上的音樂家鄰居拒絕了葉石濤父親的建議
葉石濤與父親找鄰居商量牆面拆除重建的建議,卻踢了鐵板,吃了憋!然而,葉石濤卻開始留意音樂家鄰居,並得知其為了理想而不願意妥協於現實的境況。他如此形容他:「驕傲的藝術家、有著纖細如絃的神經、容易損傷的心。生活的不如意、女兒的瘋狂、接二連三的蹉跎和挫折,使得他背負著一個巨大的創傷。」最後,在一次颱風過境之後,瘋狂的女兒摔碎了代表理想的大提琴,音樂家哭了,卻不知是為了女兒所哭,還是碎成片片木屑的琴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