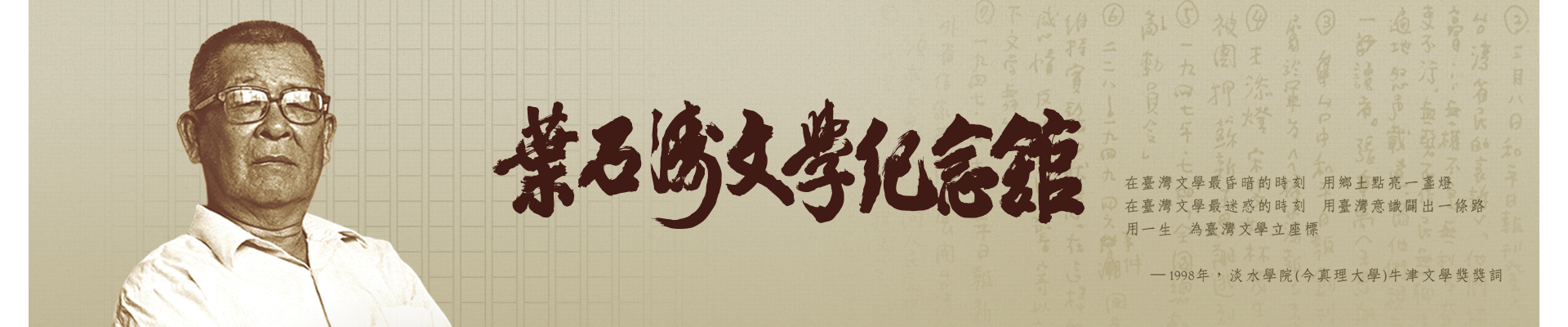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巧克力與玫瑰〉
米街是台南府城最古的老街之一,以它的街名而言,可能是清朝時代米商盤踞的地方;不過,是否真的如此,我就沒有多少把握了。這一條老街是聯絡「范進士街」與「番薯簽市」的捷徑,所以倒是相當熱鬧的通路。我的青春時代大約五、六年時光跟這米街發生了很大的關係。說是米街,其實是路寬不過三、四公尺的老街,兩邊的老舖賣的東西五花八門,當然也有一、兩家米店,但是好像賣香燭冥紙之類的店舖特別多。原來清朝時代的台南府城猶如歐洲的基爾特(guild)組織一樣,同行同業群居在一個被劃定的特定區域營生。這只是想想現今的台北迪化街專賣南北貨的情況就不難想像了。台南府城的古老街名裡有「鞋街」、「打銀街」、「代書館街」、「馬兵營街」、「草花街」,顧名思義,一定是和這「基爾特」組織的行業名有關係無疑。
義大利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日本軍閥在南洋戰場節節敗退的那一年,我已經十九歲,對於在台北幹《文藝台灣》雜誌社助理編輯的工作覺得心灰意懶,也就辭掉了這份工作,回到故鄉台南府城來。太平洋戰爭末期中,日本軍閥兵力缺乏,許多日本人都被徵當兵去了,所以他們留下的職位空缺相當多。在地方基層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要謀得一份餬口的工作並不困難。特別是國民學校裡正鬧教員荒。我喜歡讀書,又討厭跟陌生人接觸,對金錢的來往此類營生更深惡痛絕,所以再三考慮之後,決定去當國民學校的「助教」。剛好我一個堂兄是真正任官的「訓導」,是穿官服佩劍的,經他介紹,只憑我一張寥寥幾個字的「履歷表」就獲得一紙派令,命令我向「寶國民學校」報到。日據時代要謀職,似乎不需要提出任何證件,連張照片也不用繳,只憑一張親手寫的「履歷表」就通行無礙了。「助教」不具有正式教師的資格和身份,不是當官的,大約是長期代理教師之類吧。但是薪水每個月四十二元,另加「戰時津貼」大約可以拿到四十八元左右,比普通民間的白領階級的收入毫無遜色。更重要的是社會上的身份地位極其崇高,受人尊敬,活得很愜意。
我初當助教就決心留頭髮,不像當時的所有青年一樣一律剃成光頭。日本人的仗越打得吃緊,越把台灣民眾管得嚴,那皇民化,那法西斯作風,那一副統治者的跋扈嘴臉,令人難受。他們嚴禁青年留髮,一律向軍人看齊,要人穿軍服一樣卡其色的「國民服」,腳穿再製橡皮鞋。我唯一能反抗的是反其道而行,特別留長髮,光光鮮鮮地上油,又做了一套麻布夏季西裝,天天招搖過市。每當那有一雙狗眼看人低的日本校長看我的時候,他總是心痛如刀割,恨不得一口把我咬死。他屢次勸我剃成光頭時,我總是理直氣壯的引用孟子的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云云,顧左右而言之,叫他知難而退。原來日本人也通曉中國經典,且以儒教倫理治國,毀損身體違反孝道,也是他們的禁忌之一。我這番理論,似是而非,但他無力駁斥。
由於我是唯一留西洋頭的,所以不久我有了綽號,學生叫我為「High collar先生」,意思是說「時髦老師」。
我和上面提到的米街發生深厚的關係,是因為我在寶國民校任教,回家途中必須穿過米街的關係。由於寶國民學校位於「大統街」,自然我的活動範圍也就跟「番薯簽市」、「鴨母寮」、「米街」、「普濟殿」、「寶美樓」、「大舞台」發生關係了。至於「范進士街」、「武廟街」本是我外媽家所在,幼年時我常在這兒一帶徘徊流連,所以我在這一帶如魚得水,到處有熟悉的景物,熟悉的朋友,一條街還沒走完就有可能碰到一籮筐有趣的故事。別人身上發生的故事很好玩,但是臨到自己頭上就不那麼好玩了,而且有時候會教人傷心欲絕呢。
我當上助教不久的時候,有天進來了一位新助教,是個女的。年紀跟我差不多一樣大,穿著白衣黑裙。那時代的年輕女子很少穿裙子的,多是穿燈籠褲的居多;這是「戰時體制」下的裝束,日本人很有團隊精神,大家雖都認為燈籠褲不美觀,會失去女性的嫵媚,但不敢有所異議,照穿不誤。我以為這新來的女助教是日本人,也就不太理會她。一來她講的是一口蠻好聽的「奈良腔」日語,二來她的舉止動作非常拘束謹慎,又姓「井原」,怎麼看也不像台灣人。她的臉淺黑,特別是那挺拔的鼻子,令人憶起了愛琴海希臘民族的古典性秀美。她真的是難得一見的美女,她纖細的肢體洋溢著羚羊般活潑的氣息。
既然是日本人,我也就懶得跟她搭話了。而且她教的是三年級的女生班,我教的是六年級的男生班,很少有機會交談,更扯不上任何關係。
學校快要放暑假的時候,我阿母叫我回家時順便在「石鐘臼」替她買一、二斤芒果,我就走進那陰涼的米街來。「石鐘臼」就在米街街頭。這兒是攤販密集處,府城人喜歡吃的點心,如米糕啦、魚丸湯啦、炒鱔魚啦,一應俱全。
快要出米街的時候,我聽到背後有一陣輕快的履聲追上來。
「High collar先生,你到哪兒去?」那是清脆的道地日本「奈良腔」的話。我做夢也沒想到,她就是那日本女助教。
「咦,井原先生(老師)您怎的到這兒來?」我的意思是說,這是屬於台灣人的街,日本人怎會到這兒來?
「我住在這兒啊!」井原先生笑嘻嘻的俏皮地答道。
「嘿!」我搞不懂了,「您們好像從沒有人住過這兒的啊?」我的意思是說,日本人跟這台灣古老傳統地區是毫不相干的異類。哪裡知道,那井原女助教嘻嘻……的笑出聲來。而且用道地府城腔調的台灣話說:「你看不出來嗎?我是府城人啊!改日本姓名而已。我本名叫謝秀琴。」
「難怪,您臉色黑!」我報以一箭之仇,驟然發現這名叫謝秀琴的女子是有複雜心思的女人。她在學校裡拘謹而不苟言笑原來是裝出來的,她的個性一定是奔放熱情無疑,否則也不會在路旁隨便叫住我閒聊。
「我從小被送到日本奈良去讀書。在日本待了十多年。家父是牙科醫生,就在這拐彎的地方有診所。牙齒疼了就來找家父吧。」謝秀琴嫣然一笑,把發楞的我留在一家賣鐵鼎鍋的陶器鋪前面揚長而去了。我目送她白衣黑裙的纖細背影,忽然有一股莫名的情感猛地衝上胸口來。
漫漫夏日,我每天必到米街去徘徊。這不完全是思慕謝秀琴,十之八九是去找住在米街的老詩人李涵文先生。他是教古文開書房的。我和李先生談得來,所以常去找他請教唐朝傳奇小說的細節。有一次,我無意中提到謝秀琴的父親謝名貴牙醫,那李老先生很不屑的在鼻子裡連哼了幾聲,咬牙切齒的罵道:「哼!那三腳仔,看你能橫行跋扈到幾時?改姓名!豈有此理!」
我也偷偷去謝秀琴家觀察了幾次。她家是二層洋樓,從大門一進去就是候診室,常看見謝醫師正在拿鑷子之類的東西,把人家的牙齒挖挖補補。謝家最奇特的地方是她家後院子。那兒放著一個狗屋般的鐵籠子,可是關的並不是狗,而是一隻瘦巴巴的黑豬。這黑豬終日把鼻子埋進飼料槽裡哀哀鳴叫。好像吃不到什麼飼料,長不出肉來。那時候,米糧都是配給,甘薯是常食,當然也沒甚麼東西可以餵牠了。我覺得很納悶,堂堂一個醫生家不養狼犬而養黑豬,這太不體面了些。然而,我從沒遇到過謝秀琴,只看見二樓她居室的陽台有幾盆盛開的紅玫瑰花隨風搖曳。
學校開學之後,我對她的思慕越來越深,弄得茶飯不食,很想抓個機會接近她。我苦苦思索,得到一個結論:這樣物質匱乏的時代,我能夠弄到一盒巧克力糖送她,可能有效獲得伊的芳心。我四處張羅好不容易從日本空軍基地的飛行官得來了幾條巧克力;這是犧牲了我巴托克(Bart’ok)的三張愛心唱片去換來的。另外,我從小阿姨處討來了一束珍貴的黃色玫瑰花,悄悄的推開了井原先生教室的後門。學生放學後的教室寂然無聲,出乎我意料之外。她把頭伏在教桌上,似乎在哭;我似乎看到她的兩個肩膀在微微抽動,也聽見有些似有似無的嗚咽聲。
「井原桑,你怎麼了?」我猶如被空氣槍擊中的鴿子般手足無措地站的。我的巧克力和黃色玫瑰花現在倒像是嘲笑我似地在桌上放著明亮耀眼的光。
「叫我謝秀琴好嗎?」她驀地抬起頭來定定地看著我,用嚴厲的聲音責備我。我看見幾滴晶瑩的淚珠正從她的眼眶滾落下來。
「好吧,秀琴桑,我是來送你花和巧克力的。」我說。
「謝謝!」她顯得冷漠。
「你不喜歡?」我生氣了,「我差點要向那中尉下跪才換來的喲。」我委屈極了。
「我知道,你願意為我做任何事,不是嗎?」她用台灣話,脹紅了臉,害臊不堪的說。
「你下次儘管來找我好了,我喜歡你。但別再去張羅甚麼勞什子了。不過,我們永遠是好朋友,不可能變成別的。」她臉色蒼白的說。
「為什麼?」
「因為我早就訂了婚,過了年就要出嫁了。」
「跟誰訂了婚?好讓我知道祝福一聲。」我不心甘情願,咬牙切齒的說,當然一點也沒有祝福的意思。
「這與你無關。我也不想請人喝喜酒。父母之命難違,你懂得的。」謝秀琴冷冷的說。
我傷心欲絕地離開教室,當然後來也儘量設法不同她見面。但是米街我還是要去的。我有時也去看看那她家後院狗屋裡養的瘦巴巴的黑豬。秋天過去,年暮到,黑豬出乎意料之外一下子長的又肥又壯了。不知那謝醫師用了甚麼妙計養大的。
十二月中旬謝秀琴辭了職。她並沒有向我打個招呼;這也難怪,我連她的朋友也不是。新年過後我聽到同事說起她嫁給總督府的一個日本年輕官吏,而且是某個帝大畢業的。總之,她不愁沒有巧克力糖吃了。
那條黑豬當然在喜宴時餵飽了日本高官的肚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