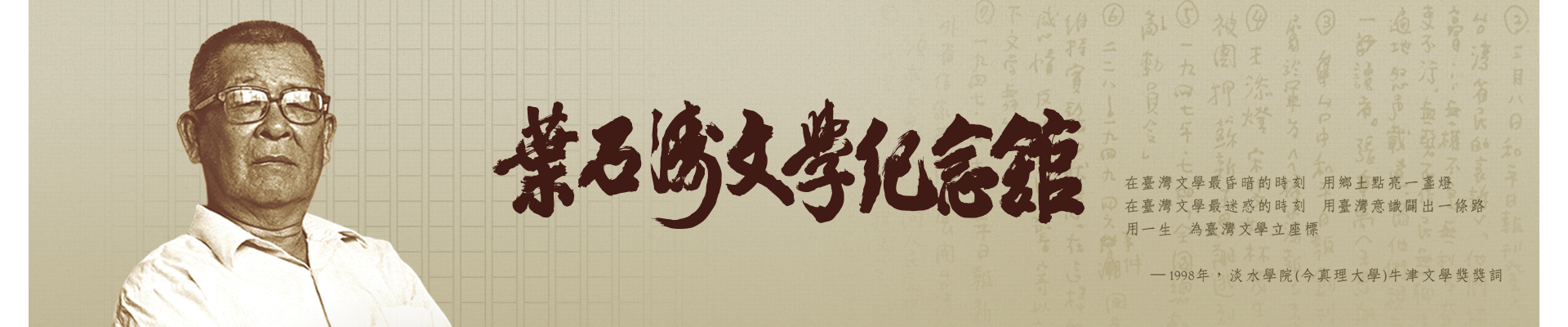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節錄自〈葫蘆巷春夢〉
本來葫蘆巷是以典雅、淫蕩著稱的;它之所以獲得典雅的聲譽大概是由於從前有一個號稱前清舉人的施三口居住在這而以相命為主,信口胡謅了〈葫蘆巷竹枝詞〉二十首而得來的,至於為甚麼獲得聲名狼藉的淫蕩這一類讚辭委實無從考察。不過,相傳有一段時期,這而是文人騷客尋花問柳的好所在,而且的確也有幾個地方仕紳在這兒金屋藏嬌,度過那風流倜儻的生活。因此,這淫蕩兩個字,葫蘆巷當受之無愧了。
然而,現今的葫蘆巷實在是令人洩氣的地方;它是一條愛湫隘、邋遢的巷路。它可悲的慘況不由得令人搖頭嘆息;由於房屋毗連,人丁甚旺,到處傾倒垃圾,杜塞的陰溝溢出的汙水無處不流瀉,使人找不出一處可以落腳的乾淨地方。而且終日街上飄盪著刺鼻的異樣臭氣,叫人不得不掩鼻而過。在狹窄的巷路中,肆無忌憚地擲球,跳躍,放鞭炮,叫嚷,喧囂的眾多小孩,他們惡劣的行為令人髮指,有時被惹得憤怒無處可洩。據說,曾經有打扮入時的高貴仕女在這兒漫步,受到年輕小伙子的調戲和譏笑幾乎昏迷過去。然而葫蘆巷真正陷入絕境,是由於人畜雜居而開始的;這禍首當是前清舉人施三口的第三代嫡孫,仍然以賣卦為生的施老頭子無疑。這老頭子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在家後院子養起豬仔來,遂釀成一種時髦的風尚,不多時前呼後應,家家戶戶養起豬來。從此處處可看到瘦如黑狗的豬仔到處亂闖,爭食,拉屎尿,這境況愈發令人慘不忍睹了。
我所租賃的二樓斗室剛好位在施老頭的隔壁,因此每當我打開窗,赫然映入眼簾的是這食慾旺盛的一群豬仔把巨大鼻子埋進飼料槽裡爭先恐後地搶時的情景,這常常使我底詩情畫意倏地雲散霧消,一筆勾銷了。我只好趕緊關閉窗戶,埋怨命運蹉跎,囊空如洗,無法擇善而居的境遇了。這二樓被隔成幾間鴿籠似的小房間,我底左芳鄰為婀娜多姿的舞女林茉莉小姐,常常三更半夜躡手躡腳的回到窩來,刷牙漱口,唱一些淒艷的時代歌曲以長噓短嘆結束而驚醒我底清夢。右芳鄰為一個安靜如處子的學生江濱生,帶著一付四百度的近視眼鏡,房間裡終日靜悄悄的,不過我老搞不清楚他讀的是何種學校,只見他一清早腋下挾著幾本洋書匆匆地走出去,將近掌燈時分又垂頭喪氣的回來。每當我從他半關的房門口走過,就常常看到他虎視眈眈地俯視施老頭子的豬舍,好似那而躲藏著陰險狡黠的敵人,非常時予以嚴密監視不可的樣子。他有時給我底履聲驚醒回頭過來慘然一笑,算是他對我慇懃的寒暄。
東方剛成魚肚色,我便起床,趕忙抓住一把草紙往公共廁所跑。在那裏我幾乎會遇到所有葫蘆巷的住民;男性公民一律面容枯寂,低頭沉思,頗有哲學家的風度。女性公民即手提潔白光滑的琺瑯質尿瓶排隊等候,吱吱喳喳地講個不停,猶如在那電線上浴著蒼白晨曦啁啾不已的麻雀。經過一番彬彬有禮的互相讓步,我總能僥倖獲得一席之地,心滿意足地蹲跨在那臭氣薰人的茅坑上,驕傲的排泄昨天未昇華為血液的廢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