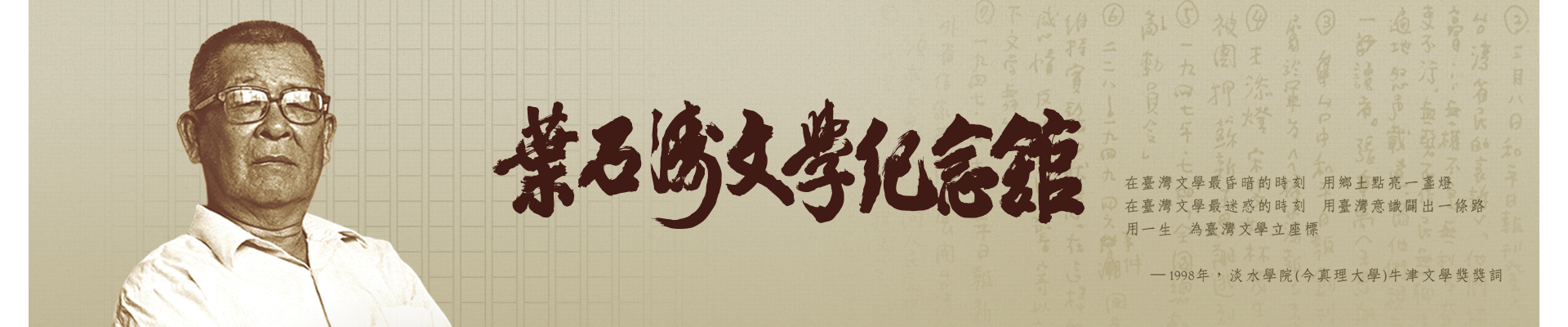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母親──戰鬥天使〉
我的母親名叫林(毛灬)治,生於民前十一年,也就是光緒二十七年,離開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的台灣割讓,已有六年。但是滿清王朝還沒有結束,直到宣統三年才壽終正寢,所以她雖生為日本人,其實還在滿清王朝的陰影下度過了幼、少年時期的十年時光。她去世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所以她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共活了八十七年。好像母親娘家的人都很長壽,母親的大哥今年才去世,一口子年九十九歲。
我的母親活的這八十七年是台灣歷史上最富變化的時代。從滿清末年的極端封建主義的社會進入異族統治的殖民地社會,再迎接了光復,重新回到祖國懷抱,她目睹了台灣民眾追求「政治的、經濟的、社會」解放的意願逐漸實現的流程,她的生活裏一定充滿了許多驚奇和刺激。當然也充滿了眾多的挫折和辛酸。但,大致而言,她漫長的一生倒是風平浪靜的;我的意思是說。她是個相當任性、開朗而堅強的女人,大多能按照她一己的意願去過活,所以活得相當愜意。浮生若夢,一個人能按個人的性格和意願去過這一生,而又能貫徹始終,這也算是莫大的福氣了。
我的母親生在古老的台南府城范進士街的官宦人家。我的外公滿清末年時正在嘎瑪蘭當縣官。乙未的台灣割讓,日本侵台軍在澳底登陸,嘎瑪蘭首當其衝,受到兇悍的北白川宮侵台軍的攻擊。據說,外公的確拚命抵擋了一陣子,終於彈盡糧絕,「棄職潛逃」,僥倖得保存一條老命。狼狽不堪地逃回府城。滿清時代
做官的知識份子,大多通曉藥理,逃回府城之後,外公就開始替人看病另開了個漢藥鋪。本來做官的,比一般老百姓是有錢的。外公的產業本很不少,後來又兼做漢醫,來抓藥的人絡繹不絕,確實成為地方上有名望的富裕人家。以外公的這種經歷而言,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應該是牢不可破的,事實上也是如此。母親取
名為毛治(招弟)。就有這個味道,而且從小就受過纏足之苦,晚年也常咬牙切齒的提到這段往事。幸好,日本天年的來臨。使得她的苦難提早結束。領台以後的日本殖民政府,很不滿意台灣人這種纏足的陋習,想盡辦法予以禁絕。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也要推動台灣的近代化,極力鼓吹台灣人小孩去接受公學校教育。
但是以當時的情況而言,台灣民眾寧願把子弟送到書房去接受古文教育,也不肯去唸那異民族的丫、一、ㄨ、ㄝ、ㄡ的番仔話。於是,公學校的學生稀少,幾乎面臨關門。那時代的國小教育不是義務教育,除去要買一整套制服、制帽、皮鞋之外,還得付出昂貴的學雜費,這些過重的負擔,無論如何,赤貧的台灣民眾是
付不起的。因此,日本殖民地政府也就選了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士為「學務委員」去推動小學教育的進展。學務委員必須勸誘人家子弟若干名去上公學校。我的外公,不幸被選上這項麻煩的「學務委員」。只好硬著頭皮去說服人家。男孩子倒也能勸得上幾個,至於女孩嘛,這就一籌莫展了。人家都說,看你肯把毛治送去唸書,我們就跟上。這一來外公為了對統治者有一個交代,不得不把我的母親送去唸書。既然要去唸書就不能纏足了。所以母親的雙腳也就得到解放,她的腳也就歡天喜地,重新自由自在地生長起來。不過,既已受到摧殘,她的腳也只能長到天足婦女的三分之三大罷了。不幸,在公學校裏的運動會她參加了賽跑,跌
了一蛟。扭傷了腳踝,我的外公的醫療卻不見效,從此以後,我的母親一輩子走路就有點不方便了。
生長在這樣封建氣息濃厚的舊式家庭裏,,表面上看起來我的母親應該是三從四德為美德的舊式婦女才對。其實並不盡然。她是非常任性而富於反叛性的人。這種個性大約是來自天性,也就是遺傳。外公當然是循規蹈矩,滿腦子儒教思想的人,不會遺傳給她這樣的資質。她的個性來自我的外媽,就是外公的細姨。
外媽可能是來自草地的查某嫻(ㄚ鬟)升上來的。我的大舅也是她生的。既然,外媽來自草地,大概也保存了由唐山來台灣開闢新天地的移民那一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險犯難精神的吧。這是我母親之所以終其一生擁有能看透社會新潮流,絕不反對任何新生事物的精神的緣故;否則,她也不曾放任我一輩子浸淫在毫無指
望的文學裏打滾了。其次,她受過日本人六年的小學教育,學到了較文明而嶄新的觀念。她懂得男女生而平等,迷信必須打破,追求個性獨立自主的態度。她聽懂日本話,看懂日本文,也會講日本話。可是我很少聽到她講日本話。在另一方面,她因家學淵源也懂得古文,所以嫁到葉家以後,凡是和日本殖民地衙門打交
道時,都由她出面。她是常拋頭露面的;葉家的田產不少,凡是辦理有關田產、稅金等事務或和佃農打交道,非她出馬不可。這並非她一個人如此,是台灣社會的風氣使然。原來,台灣自古以來是個移民社會,女人也是重要的勞動人口,從篳路藍縷以開拓荒地以來,台灣的女人一向是和男人並肩作戰的。在台灣歷史上
,台灣婦女始終是「戰鬥的天使」,擁有相當的行動自由和自主性。這在封建的唐山,是很罕見的。所以台灣婦女濃妝艷抹,招搖過市是司空見慣的。李鴻章不懂台灣社會的歷史誣蔑台灣為「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地方,這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的母親在二十四歲時,嫁到葉家來。我的父親當時二十六歲,以早婚的那時代而言,這實在是太晚婚了些。這大概是要選擇門當戶對以及教育程度的關係。葉家以其府城的地位、資產、名望而言尤勝林家一籌。我的母親是公學校畢業,父親也是公學校畢業,在那時代而言,都是受過日本新式教育頂尖的小知識份子。我的父母思想非當開明,只注意讓子女受良好的教育,至於興趣和思想取向都不加以干涉,讓子女自由發展,這很有效地使子女個個有了相當的成就。在那日本殖民地統治時代,六個子女個個都受到一骨中以上教育是很難做到的。
在日據時代的五○年四個月,是母親活得最平安的日子。這多少和經濟安定有關係。由於日本人壓榨台灣農民,始終站在擁護台灣資產階級的這一方,所以擁有田產的地主階級的生活是相當有保障的。我家一方面有一點田產,此外父親也在吃頭路,所以生活小康,三餐無憂。我的父親是頂沒「出息」的人。幾乎同
我一樣。他也是一個文人,家裏的事一概不管。甚至連子女的教育也很少過問。所有家裏的大小事務,從廚房雜事以至於跑日本衙門等重大事情統由母親一手包辦。六個子女的大大小小瑣事已經叫她夠忙了,還得跑到草地去看田地收成,這不叫她不拋頭露面是不行的。於是,在我的記憶裏留著的深刻印象是母親濃妝艷
抹,著民初婦女裝,打著斑爛陽傘,牽著我的手,到府城的銀座「林」百貨公司去替我買衣服時的那青春,美麗的風采。我的母親愛打扮,喜歡追逐流行的癖氣從來不改變。八十六歲時。我把她奉養在左營家裏,她已經中風兩次,行動不便,仍然會蹣跚地橫過車水馬龍的馬路到對面的「羅曼斯」髮型工作室去,或燙髮
,或洗髮,總得要修飾一番。我很不放心,請她少去,她會發脾氣,大罵我一頓。
說她奢侈嗎,也不盡然。她也很會吃苦耐勞的。她頂愛享受,但也很會吃苦。光復後,土地改革的推動,使得我家所有田產一去不回,家道衰落。我又沒出息,光靠一份小學教師的薪水尚且養不飽一家四口,哪有餘錢供她過得舒服。因此有一段時期,她只好幫人家洗衣服度日。我常說她,粗菜淡飯還可以吃得起,何必去賺這麼辛苦的錢。但是她絕不接受我的苦勸,她總是把辛苦掙來的錢,毫不吝嗇地痛痛快快花掉。這是她的個性,任誰也改不了。其實,子女們孝敬他的錢不少,普通的老人家日常的花費也盡夠了。但是,她總得要自己去掙錢,否則閒下來似乎很痛苦的樣子。
她一輩子愛喝酒,喜抽煙,整天煙不離口。而且,不喜歡吃蔬菜水果,吃的盡是魚和肉。特別喜愛鹹食物;舉凡豆鼓、醬瓜、鹹肉、鹹魚之類的食物最合口。她有嚴重的高血壓,但子女的苦勸都無效。八十多歲的時候跌了一跤。從此健康每況愈下,但仍然我行我素,從不改其樂。抽煙照常,吃鹹東西照常,中風兩
次,躺在醫院好幾個月也從不埋怨。好像她一點他不怕死,真的是視死如歸。
八十七歲初夏的一個清晨裏,在台南府城的一家療養院,她第三度中風,從清晨到深夜十二點,她的意識從沒有恢復過來。她本來已經是半植物人了,這一下,大概她頑強的生命力也不得不向死神投降了。我整天守著她,看她滿是皺紋,刻著台灣三個時代多難歷史的臉。心裏淌著血,很清楚這是我們母子最後相處
的時光了。雖然她嚥了最後一口氣,但我覺得她並沒有離去;因為她就是我,我就是她,我們是分不開的。即使她離開我的時候,沒說過話,但我心裏很明白,她已經原諒了我這不肖兒子的沒出息。她應該覺得高興,我的生命就是她的生命的延續;她一輩子按她意願自由奔放的過了一生,而她的兒子也跟她一樣按自己
的意願差不多將要過完這一生。我這一輩子沒什麼成就,但起碼跟她一樣,愛做什麼就做了什麼,無怨無悔,毫不受人家制肘。否則也就不會樂此不疲地寫了勞什子文章幾達五十年了。